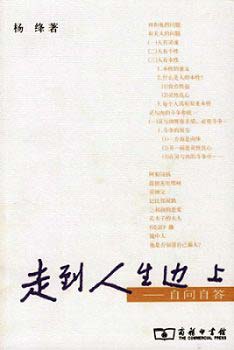
《我们仨》中,杨先生用“古驿道”暗喻人生似旅途;《走到人生边上》同样喻人生为渐行渐远的旅程。作者已经九十六岁,她走在夕阳西下、暮色苍茫之中,回望来路,斯人已逝,多少前尘旧事,魂牵梦绕,难割难舍,难断难了。从《写在人生边上》到《走到人生边上》,岂不是在生命的暖流中,两个默然相契的灵魂长相守望,超越了时间空间,超越了阴阳生死。如此这般的“夫唱妇随”,令我感动莫名。
《走到人生边上》是部领军之作、升华之作,和杨先生以往的作品大不相同。全书编排分为两个部分。杨先生称前半部四万余字为“本文”,将后半部十四篇散文冠以“注释”之名。就是说,前半部是主体,是文本;后半部是文本的注脚。本文与十四篇散文之间,形成 “六经注我,我注六经”的非常格局。这样的阐释方式可谓是别开生面,前无古人。
“注释”部分读来备感亲切。它们是我熟悉的风格,喜爱的笔墨。阿菊闯祸险酿大火;喜鹊夫妇筑巢之勤,丧子之痛;三叔叔的家庭悲剧;秀秀为亲人无私付出,回报却是亲情的疏离和背叛,等等。作者平实写来,却动人心魄,犹如阳关三叠,一唱三叹。其内容呈现的善善恶恶、是是非非,又无不与前半部的本文相契合照应。杨先生之冠名“注释”,很是贴切,很是深刻。
本文部分文风一变,夹议夹叙,开合自如,纵心而论。议论时虽然旁征博引,却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论文;叙述时文笔灵动,旨归又紧扣议论。阅读之初我颇为惊讶,稍有陌生之感。细读下来,又颇多新鲜之感。在不大的篇幅中,作者议论所及,都是古往今来的大命题、大难题。诸如:生存死亡、神灵鬼魅、肉体灵魂、宗教信仰、道德良心、人生价值,等等,不一而足。无论拈出哪一组论题,相关著作早已汗牛充栋,古今中外多少大士哲人、专家学者毕其一生殚精竭虑而至今仍然莫衷一是。可以断言,未来若干世代辩论也仍将继续,未有穷期。
中国文士论学养推崇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杨绛先生可以称得上是兼具两“万”的耆学宿儒。或许她更多此一筹:她即将登临生命的珠峰—— 一百岁,而且至今未见有高山缺氧反应。她依旧思路清晰,下笔琳琅。她在本书中涉及如此之多的人生哲理,气势宏大,却无意强作解人,一一得出终极结论。作者凭借她过人的聪明才智、深厚的知识学问、丰富的生活阅历、惊人的毅力勇气,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去思索,去感悟,去质疑,邀约读者对生命多一分关爱,对灵魂多一分修炼,对命运多一分敬畏,对良知多一分守护。
《我们仨》是至情之作,读者要用情去阅读,追随作者歌哭,体味人间至爱,达于至真。《走到人生边上》是至理之作,读者要用心去阅读,追随作者思考,求索人生真谛,“止于至善”。
《听杨绛讲往事》
吴学昭执笔的杨绛先生传记《听杨绛谈往事》由三联书店出版。在这部“获得杨绛先生首肯”的传记里面,读者不仅了解到杨绛先生从儿时到98岁所经历之种种,也感受到杨绛先生的淡泊气韵。
初遇钱钟书
1932年初,借读燕京手续办妥,阿季与父亲商量要北上借读。父亲不大放心,说:“你若能邀约到男女同学各三人同行,我便同意你去。”阿季果然约到周芬、张令仪两女生,孙令衔、徐献瑜、沈福彭三男生。张令仪本约定同行,但她临上火车赶到车站,变卦不走了。
1932年2月下旬,阿季与好友周芬,同班学友孙令衔、徐献瑜、沈福彭三君结伴北上。那时南北交通不便,由苏州坐火车到南京,由渡船摆渡过长江,改乘津浦路火车,路上走了三天,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上。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,原来是费孝通,他已经第三次来接站,前两次都扑了空,没见人。